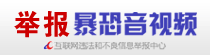十月的金秋是收获的季节,儿子上大学那年,母亲在小院里移栽了一棵枣树。她亲自浇水、施肥、剪枝,一晃四年过去,如今那棵枣树进入盛果期,红彤彤的枣儿,挂满枝头,迎风摇曳,引来鸟儿的垂涎,枝桠间漏下斑驳的晨光,恰好将母亲佝偻劳作的身影映成一幅流动的剪影。
天微亮,母亲早已起床,把家和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,打扫得干干净净。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,要内外整洁;既昏便息,关锁门户,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……”她握着竹扫帚的手布满薄茧,却仍能准确无误地哼出《朱子家训》的曲调。青石板上的露水被扫成蜿蜒的溪流,檐角的蛛网在晨光里晶莹如丝。
这是生活的歌,她用这首歌,唱出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。
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铁锅,玉米糁粥的甜香漫过窗棂。当丈夫踩着露水推开院门时,饭桌上已摆好冒着热气的南瓜蒸饺。这个皮肤黝黑的泥瓦匠将安全帽往桌上一放,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工地的尘土。
“今天有喜。”母亲指着檐角喳喳叫的喜鹊,鬓角的白发在晨光里微微发亮。她总说儿子是带着书香门第的福气来的,当年高考落榜的遗憾,在儿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,化作了庭院里新栽的枣树。
暮色四合时,儿子风尘仆仆地推开院门。他晒黑的脸庞泛着兴奋的红光,书包带子上还沾着省城的梧桐叶。母亲特意温了一壶米酒,琥珀色的酒液在粗瓷碗里荡漾,映着三代人各异的神情。
“爸妈,我被用人单位录用了。”儿子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雀跃,“每月三千。”
父亲手中的烟杆“咔嗒” 磕在砖地上,火星溅落在青砖缝里,如同他眼里明灭不定的失望。
“工地小工都挣四千五。” 这个在脚手架上讨生活的汉子,总觉得大学文凭该值更多钱。他粗糙的拇指反复摩挲着碗沿,仿佛在丈量知识与体力的兑换比例。
母亲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,目光却像钉子般钉在丈夫脸上:“老东西,尽说些风凉话,人家以后工资能涨,你呢?到头了……”
“现在大学文凭不吃香了……”父亲说完,唉了几声。
母亲接着说:“不吃香也得有文化,没文化的发展就像坐着牛车。伟人曾说,‘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,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’”
父亲在烟灰缸里碾出深痕,沉默像一块沉重的磨盘。
母亲突然笑了,眼角的皱纹漾开温柔的涟漪:“儿子这一代人是用知识装备自己,而我们那代人全靠体力打拼。总有一天,儿子会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产品,那时,我还要跟儿子好好活几年呢!你看那枣树,刚栽时细得像根筷子,现在不也能遮风挡雨了?”
月光爬上枣树的枝桠,在斑驳的树影里,三个人的影子渐渐叠在一起。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,仿佛在丈量着知识与土地之间的距离。母亲轻轻抚摸着枣树粗糙的枝干,她知道,有些成长需要等待,就像有些果实,注定要在秋天成熟。(开阳君)
编辑:张钰